2021/1/1
侯崇文 榮譽副總會長 國立台北大學前校長 :社會事實的修復式正義及其實踐﹗前言

侯崇文 榮譽副總會長 國立台北大學前校長 :
社會事實的修復式正義及其實踐﹗
前言
一,修復式正義是一個古老的觀念,卻是近代學術發現
用和解的方式處理衝突問題,世界各國都有,且也都存在很長時間,只是,把和解作為專業的,以及視為科學研究領域則是晚近的事。
美國兩位於教會從事監獄受刑人,家屬,受害人的協助者,Daniel W. Van Ness與Karen Heetderks Strong博士,寫了一本暢銷書,修復式正義簡介,Restoring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to Restorative Justice,他們指出,修復式正義約於1980年代出現,由一個正義團契(Justice Fellowship)團體發起,這團契屬監獄牧養教會(Prison Fellowship Ministries),Van Ness 與Strong兩位都曾服務於該教會。
Van Ness 與Strong和教會人員,共同合作推動修復式正義,他們首要任務為找出修復式正義的原理原則,後來他們發展了三個基本原理,第一,確定修復過程 (restorative process),指受害人,加害人,以及相關的個人或社區成員,透過促進者,共同尋求犯罪帶來問題的解決。第二,強調修復結果(restorative outcome),表示修復過程在於取得大家同意的結果。第三,對當事人(parties) 的定義,乃指受害人,以及任何因為犯罪受到影響的個人或社區成員者稱之。其後,他們投入研究,並有系統的出版修復式正義有關理論的著作,也同時出版修復式正義實際運用上的指導手冊。1997年,他們正式出版修復式正義,目前已進入第五版,他們的理論與做法深受好評。
澳洲社會學者John Braithwaite 以一個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的島嶼國家,巴布亞紐幾內亞 (Papua NewGuinea) 為例,強調,在那裡的社區與犯罪或違法帶來的衝突,彼此並不對抗,他們的衝突可以用一種交換的形式解決,進而恢復關係,建立秩序,也能得到正義。巴布亞紐幾內亞解決衝突的方式是修復式正義,暴力報復或法律懲罰並非解決衝突最佳方式,透過和解,達成協議,也可修補犯罪帶來的不正義問題,同時也在於避免社區衝突關係的惡化。但是,如果發現衝突和解並非最好做法,社區的不正義仍然存在,這時,修復式正義則是沒有必要的。例如,強姦的不正義,對社區來說,可能需要用懲罰作為反應;而對於極端暴力,傷害社區太大,修復式正義無法帶來正義或嚇阻犯罪時,監禁似乎是最好的方法。
我父親擔任嘉南農田水利會工作站主任,有一次兩個農夫為了水源,在田裡發生衝突,有一個人拿起鏟子把另外一個人打死了。這衝突件事後來由我父親出面協調,雙方以賠償解決,沒有進入司法,因為大家都不願意因這事故繼續受到傷害,這樣做對整個社區也是最好的。相信台灣不管是早年或現在都有許多用修復式正義解決衝突的例子。
臺灣的和解政策以區公所的調解委員會最為人所知。他們調解民事事件,例如:債權債務的清償、房地產買賣糾紛、租賃關係、佔用及婚姻糾紛等,其中以車禍求償的調解最多,此外他們也調解刑事案件。調解委員為地方上具有聲望的人士,他們不必具專業調解的訓練,因為達成和解即不再訴訟才是他們最大的目的,這與修復式正義的精神存在很大的差異。
政府的調解事件,107年各地區調解委員會所辦理的調解業務高達14萬522件,其中,調解成立者達 11 萬2,774件,比率為80.3%,且統計指出,這是歷年新高的比例,可見今日民眾日漸接受以和解解決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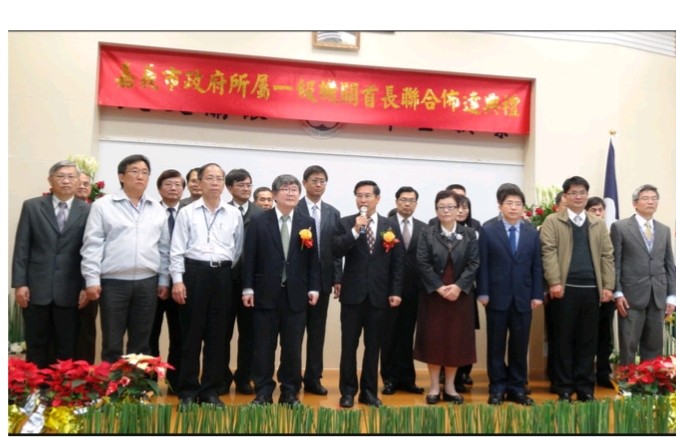
二,修復式正義有許多社會意義
修復式正義具有許多社會價值,衝突當事人,彼此透過見面、溝通,這樣的過程具有諮商價值,舒緩受到傷害的情緒,而關係的恢復,提高人們回歸社會參與的意願,對社會發展是很正面的。
而對還在成長中的小孩來說,透過修復式正義協商,學習是非對錯,也同時恢復人與人,人與團體的關係,成為小孩成長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修復式正義對小孩來說十足之教育意義。而如果涉及法律訴訟,修復式正義是司法程式上的另一個選項,可減少法院負擔,亦可縮短解決問題時間。
修復式正義是批判與改革的:修復式正義提倡者帶有高度的理想性,他們寄望透過修復式正義進行一個刑事司法體系的改革,也會是一個司法體系哲學思想的轉換,他們認為當今刑事司法體系沒有效率,也無犯罪嚇阻功能,他們寄望一個新的觀念與想法,帶來新的社會秩序。修復式正義和犯罪學古典學派學者一樣,它們是批判的,改革的,抗議這時代無效率的制度與功能,他們所提出解決方法,是一個新的觀念與想法。
澳洲學者 John Braithwaite (2003) 介紹修復式正義原理原則時就強調,從科學知識角度,或者從政治改革角度,修復式正義都涉及激進改革,不僅是刑事司法體系的改革,更是整個刑事司法體係典範的轉移,一種思想上,做法上的改革。而就犯罪學來說,修復式正義也是犯罪學理論典範的轉移,他特別指出,傳統犯罪學強調街頭犯罪的控制罪,也都依賴員警、法院、監獄制度,但他認為犯罪問題仍舊嚴重,社會問題並沒有獲得有效解決。另外,刑事司法體系標籤化犯罪人,降低加害人復歸社會的可能性,據此,Braithwaite 呼籲犯罪學應該要有新方向,且要與傳統焦點區隔,修復式正義正是這一個犯罪學理論的新概念,強調因衝突引起的傷害需要修復,以解決不安全感,他也認為修復式正義應該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運動,在於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Braithwaite, 2000)
三,台灣霸淩防制已進入修復式正義年代
修復式正義的風潮最早吹向法務部,2008年5月,由王清峰部長提出,要求研議推動修復式正義,鼓勵被害人、加害人進行對話,達成調解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VOM)。只是,被害人與加害人的調解執行,最大困難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不願意見面,這使得法務部推動的方案困難重重,成果相當有限。
2012年初,筆者與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周愫嫻、林育聖等三位教授,接受教育部委託,協助推動「防制校園霸淩」工作,辦理「防制校園霸淩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及「防制校園霸淩個案處遇作為工作坊」,讓學校輔導人員可以認知到校園霸淩的通報責任和處理校園霸淩的方法。一年之後,我們導入犯罪學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成立「橄欖枝中心」,鼓勵衝突當事人見面、相互溝通和對話、尋求和解,恢復關係,以有效解決霸淩問題,進而促進校園和諧。
橄欖枝是和平的象徵,這典故來自舊約聖經挪亞方舟的故事,「橄欖枝中心」則以建立和平與友善校園為最終目標 (侯崇文、周愫嫻、林育聖,2015)。
去年,2020年,七月,教育部正式將修復式正義概念納入校園霸淩預防,校園霸淩防制準則第4條為各級學校霸淩預防之規定,其中,第六款明訂:學校於校園霸淩事件宣導理或輔導程式中,得善用修復式正義策略,以降低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我們樂意看見台灣霸淩防制政策採用對話、溝通,以及人道精神與關係恢復的修復式正義,只是未來仍須透過教育培訓,強化老師有關修復式正義的瞭解,以及提升和解技巧與能力。
迎接修復式正義時代的來臨,以下介紹其定義,理論基礎及其內涵,也簡單介紹修復式理念於輔導上之運用。
修復式正義的社會事實核心概念
修復式正義 (restorative justice) 概念的提出是很晚近的事,學者中以澳洲國家大學教授John Braithwaite最負盛名,影響也最大。
Braithwaite修復式正義主要的作品寫於1989年的《犯罪、恥感與整合》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以及後來與他的同事Toni Makkai(1994)兩人合寫的《恥感整合規範標準之遵從》 (Reintegration shaming and 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standards)。Braithwaite稱他的理論為「整合恥感理論」(re-integrative shaming theory),他強調:恥感能發揮作用,激發不犯罪力量,「人與社區的整合」和「人受到社會支持」是其關鍵。
上述「整合恥感」論點正是修復式正義理論的核心,無論是犯罪者的矯正,或被害者受傷的彌補、療癒,都必須建立在人與人,人與團體,關係恢復與整合之上,而這正是法國社會學者Durkheim社會事實之概念,人與社會情境的連結與整合是健康社會,建立社會秩序,最為重要之依據。
修復式正義的理論實踐 - 修復實踐
修復式正義強調實踐,理論必須屈服於行動之下,只有實際採取行動,人類犯罪帶來的衝突與社會秩序的威脅才有改善的可能。如此,修復式正義是一種行動,一種實作,一種實踐,需要實際行動,用計畫與方法來改變犯罪對社會所帶來的傷害,包括:加害人、被害人,以及犯罪所傷害的社區或團體,才能達成目的。也因為修復式正義實踐的本質,犯罪學者有稱修復式正義為修復正義實踐(restorative justice practices),或修復實踐 (restorative practices) 的。
Braithwaite自己則是推動修復式正義理論與實踐的佼佼者,他長期投入相關問題研究,也身體力行,實地到受害災區現場主持修復會議,促進世界和平,也推動修復式正義社會運動的前進。
2016年六月Braithwaite (左) 參加在伊朗伊斯蘭阿紮德大學 (Islamic Azad University) Mashad校區修復式會議 (資料來源:John Braithwaite – war, crime, regulation 網站)
而作為實際行動,修復式正義有其工作原則:「促進對話、恢復關係、解決紛爭」。促進對話通常是透過第三者,稱為促進者 (facilitator),他最為重要的工作在於安排見面與對話,本質上屬於加害人、受害人及社區相關成員之間的聯繫 (connections)工作。促進者也要用一個較為非正式,且易於控制對話的方式來進行;同時,促進者也要創造一個使參與者感到舒服的氛圍,他們可以為自己或者為別人講話,這在於抒發衝突帶來傷害的感受,也是對未來雙方關係恢復可能性的努力。總之,強調加害人、被害人和社區的對話是修復式正義的行動原則,且在於修復人與人,人與團體的關係,如此方能達成犯罪矯正,建立社會秩序之目標。
修復式正義的定義
Braithwaite 這樣定義修復式正義:
「修復是正義是一種因為犯罪或不公正所帶來的傷害,任何相關的人,大家共同討論犯罪或不公正的帶來的傷害,以及如何修復關係的努力。」(Braithwaite, 2004)
Braithwaite(2019) 在個人網站上再次定義修復式正義:
「修復式正義在於修復受害者,修復犯罪加害人,以及修復社區。它的基礎是:因為犯罪帶來傷害,所以正義應該要痊癒(because crime hurts, justice should heal)。」
Braithwaite 的定義有下列幾個要素:
第一,犯罪或不公正帶來了傷害。犯罪自古皆有,但犯罪者往往帶來受害人或社區生命、財產的傷害與損失,另外,犯罪也伴隨著許多間接的傷害,心理的,人際關係的,且有些時候,犯罪的間接傷害嚴重性程度更大,負面影響也深遠。
第二,受到犯罪傷害的相關人可以是:犯罪加害人,被害人,或者是團體其他人,或是社區的人,這些都是修復式正義要處理的對象。
第三,修復式正義強調犯罪相關人共同的對話、溝通、會議、討論等。
第四;修復式正義最終目的在於得到正義,所以受害人必須要能療傷止痛,加害人必須為行為負起責任,另外,受到傷害的社區也得到正義,恢復秩序。
美國學者Howard Zehr (2015)也定義修復式正義,他說,修復式正義是一種生活,一種哲學,並以3R作為基礎,包括:「尊重」(respect),「責任」(responsibility),「關係」(relationship)。尊重是人與人彼此之間的尊重,我們必須彼此尊重對方,儘管他是犯罪者,他傷害你,傷害社會。責任是加害人行為責任的問題,犯罪者必須為他的行為負起法律的責任,也必須負起道德責任。至於關係則是人與人,人與社區關係恢復的問題。「尊重」,「責任」,「關係」,三者是修復式正義核心課題,也是修復式正義要成就的目標。
作者是社會學者,就用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 (Durkheim, 1895, 2013)社會事實[1] (social facts) 的觀點來定義修復式正義:
「犯罪或偏差帶來的傷害,透過尊重與負責任的對話,嘗試恢復人與人,人與團體關係的一種實際行動與實踐,並在於給人參與社會的能力與動機,進而達成社會秩序建立之目的。」
這裡,作者也和其他學者一樣,強調修復式正義必須面對犯罪帶來的傷害,以及必須以對話方式尋求對於衝突當事人最有利的解決方法,基本上,大家可以進行面對面的溝通、談判、協商、仲裁…,以療傷止痛,解決問題。
作者更認為,修復式正義是一種教育過程,從對話中,犯罪者體認了自己行為的責任,並學習是非對錯的價值觀,進而增進自己社會適應的能力;至於受害人,他們能從修復過程中感受到支持,並透過道歉、賠償等方式,作為受害人的補償,以使修復過程成為有意義的行為,進而願意寬恕對方,並發展出正面、積極的人生態度,重新出發。
作者並認為,修復過程在於凝聚居民共同情感,並為衝突當事人尋找可能的社區資源,讓他們有機會參與,成為社會分工中具有意義的成員,如此才是社區安全的保障;而對於犯罪人或受害人,只有他們在社會分工中有角色、功能,才能確保他們的人格發展,以及激發對這世界的正向態度。
修復式正義的許多誤解
坊間有許多解決衝突的作法,也被認為是一種修復式正義的實踐,但他們都不是,以下說明之。
一、修復式正義不是調解
我們社會有許多衝突,他們多數是透過協調、調解解決,而沒有進入法院程式,其中,組織最大者為各市區公所,以及鄉鎮公所的調解委員會,他們調解的項目非常的多,以房屋租賃或買賣糾紛,房屋漏水,交通事故傷害之賠償等案件最為普遍。
調解委員會通常聘請地方上具有聲望人士擔任,並不必具備社會科學知識,但以達成和解,受害人得到合理賠償,雙方並不再訴訟作為主要目的。但修復式正義則致力於衝突關係的恢復,並尋找資源,使衝突當事人得以參與社會分工,增強工作能力,這些都是調解委員會所沒有的功能。
二、修復式正義不是道歉,寫悔過書
2009年,法務部曾舉辦修復式正義的徵文比賽「有話對你說」,此活動在於表達加害人對於他們自己犯罪行為的認錯,並表示歉意與悔改;至於被害人部分,則希望他們在接到加害人的悔改信後,能夠選擇原諒。基本上,這樣的活動在於使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都能走出生命的陰霾 (2009/10/8聯合報),但這做法並不完全符合修復式正義精神,因為缺少中間促進對話的調停人,也缺少參與活動的自願性,更重要的,單方面的悔過書往往未能帶來雙方關係的改善。
三、修復式正義不是善意的溝通
台灣有有人推動「善意溝通修復協會」,嘗試要以醫療上善意溝通技巧來化解衝突,進行修復調解,但這不是修復式正義。
善意溝通主要用於處理醫病關係,是一種醫生與病人溝通的技巧。醫生給病人資訊,尤其是疾病噩耗的傳遞,可以是語言的,或者非語言的,善意溝通則在於平衡醫生帶來的醫學資訊,以及這些資訊可能帶來病人,或家人激烈的情緒反應。善意溝通技巧往往可以很有效的連結醫生的資訊與病人及其家屬的病情的認知。
然而畢竟醫療關係不同於犯罪,加害人、被害人的關係,醫生很有權威,他們和病人的關係不是平等的,在醫療情境,善意溝通有利於傳遞病情給當事人,或其家屬;然而,修復式正義當事人處於對立與衝突情境,第三者往往必須站在公正,平等的立場,主持會議,方能帶來雙方有意義的對話與結果。當然更為重要者,修復式正義應該更聚焦於破壞關係如何恢復的問題,大家必須向前看,讓加害人與被害人有重新參與社會與團體的動機,而這是善意溝通無法成就者。
四、修復式正義不是同理心
法律扶助基金會在網站上這樣寫著:犯罪後透過善意溝通及同理心,協助當事人療癒創傷、復原破裂關係。所以,同理心被納入修復式正義的工作原則,用同理心來激發願意原諒,願意幫助對方,而更為重要的,用同理心來達成衝突當事人的和解。
同理心(empathy)是一種諮商輔導的技巧,鼓勵當事人站在他人立場,去瞭解,或體諒他人情緒與想法,這有助於個人的情緒控制,而同理心也有助於發展個人的正向行為,使人更願意去幫助別人。同理心更是律師協商的技巧,讓當事人能從對方立場,瞭解對方的想法,以達成和解。
修復式正義從溝通、互動與對話的過程中,重新定義彼此的關係,以及重新解釋雙方的角色,恢復關係,並發展出正向對人,對這世界的態度,這才是修復式正義的價值。而在面對一個犯罪衝突的情境,同理心是否使受害人願意原諒對方,或願意恢復關係,達成修復式正義的目標,這並無直接關係。
五、修復式正義不是喬事情
台灣政治圈常聽到喬事情,政黨公職候選人,甚至於總統選舉,都聽過用此方法解決,大家協商就好了,不必透過公開的競選程式。另外,立法院對法律條文之制定或修改,經常吵吵鬧鬧,爭議不休,這時有人出面,大家關起門來,用喬的方式來使法案能順利通過。台灣早年農業社會也經常用喬的方式處理衝突,一些農人因為搶水,搶地,經常發生打架衝突,甚至於暴力殺人事件,很多時候,都由地方上有聲望的人士出面,協助雙方談妥賠償金,事情就用這方法解決,案子則不送法院。
喬是以和諧或較為和緩的方式解彼此緊張或衝突的情境,經由第三者讓雙方消除爭議,只是,修復式正義和喬的調解有很大差異,首先,喬有半強迫的意思,和解並不是雙方都同意,往往是先由協調者提出一個解決的方式,之後尋求當事人的同意,其方式可能是勸說,或政治或人情施壓。其次,喬的主角是主持人,不是衝突的當事人,這與修復式正義的精神不一致。第三,喬只重視解決衝突,並不尋求恢復衝突當事人未來的互動關係。
修復式正義的特性
- 修復式正義是人道主義的
修復式正義鼓勵對話,強調寬恕、原諒、關係修復、傷害修復等,基本上,修復式正義使犯罪人、被害人及更大社區的關係都得以修復,這也是非常人道主義的。
修復式正義反對刑法上過度聚焦於犯罪人的懲罰或犯罪人的矯正;相反的,修復式正義用更為人道的精神關懷受害者,使受害者獲得賠償,幫助受害人走出被害陰影。
修復式正義也聚焦於加害人的矯治,透過對話,認識犯罪的傷害,以及犯罪的責任,另外,修復式正義嘗試恢復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給人正向力量,不再犯罪,這也是非常人道主義的。
修復式正義並透過第三者,即促進者,安排衝突當事人,包括:加害人,受害人,以及社區相關成員,大家建立一個對話機制,通常促進者公平看待對話的每一個人,促進者也積極的創造一個較為非正式且易於控制對話的情境,以解決犯罪帶來的傷害與衝突,這些都是人道主義的表現。
- 修復式正義是社會事實的
根據塗爾幹 (Durkheim, 1895, 2013) 社會事實的觀點,修復式正義主張,「加害人、被害人與社區,三者都是修復式正義的重心。」修復式正義嘗試修補人與人,人與社區的關係,而這也是人類行為學習與改變的基礎。
Braithwaite(1994) 曾這樣寫道:
「因此,當恥感是更加的整合的,這時社會控制理論產生作用 (意謂減少犯罪),而當恥感是在一個標籤的環境,這時標籤與犯罪次文化理論占了上風 (意謂增加犯罪)。」
Braithwaite認為,一個犯罪者在犯罪之後出現了遵守社會規範的恥感,但如果犯罪者所生活的環境是一個排斥、標籤、羞辱的,這時候恥感是無法產生抑制犯罪作用的;相反的,如果犯罪者有了恥感,且他生活的環境是寬容、瞭解與接納的,這時恥感則產生抑制犯罪的作用,犯罪者提高遵守規範意願,不再犯罪。
我們看到社會事實的重要,恥感配合上團體的接納與整合,將可以有效提升法律遵從意願,而這也是改變偏差行為的力量;也因此,修復式正義強調,人必須與社會、社區,或團體結合,只有這樣,修復過程才具有意義,才能發揮改變人的作用。也因為這道理,加害人,被害人,社區三者是修復式正義的核心,修復式正義必須討論如何恢復人與人,人與團體關係的問題,三者必須整合,且缺一不可,只有受到社區的支持,人們才有展現遵從社會規範的可能。
- 修復式正義是實用哲學的
在此一實用哲學的理念下,社會學家相信世界的知識必須從生活經驗世界中得知、瞭解;因此,學者必須走入都市環境、蒐集資料,發展社會學理論,讓知識能夠幫助人類社會適應。
修復式正義相信,透過見面,溝通,互動,就有改變人的機會。修復式正義也在於促進人與人的對話,並且恢復人與人,人與團體的關係,讓人與人可以在一起,有合作,也有競爭,但更為重要的:每一個人都要有參與社會團體的能力與機會,這些都是修復式正義的實用哲學,以及知識幫助人類生活適應的價值。
- 修復式正義是實踐的
作者舉個例子,是我和一位中輟生對話實際行動的故事。我主動邀集修復式對話,這時,我請了那位中輟學生的監護人,他的舅舅,導師,班上兩位同學,一位是好朋友,一位是模範生。校長也出席會議。我們大家坐下來,我先請這位離家的同學講話,她沒有講太多,只是低下頭,眼淚一直掉。之後,我請和她最好的同學講話,她說很想念她。我也請家長講話,導師講話。總之,透過實際的行動與對話,過程中,中輟生知道對錯,更找到支持的力量願意來改變自己。
如果我沒有採取行動,就看不到這位中輟生的改變。
修復式正義現在成為全球性的社會運動,許多國家,許多的社團,都致力於用和平與人道的,用非懲罰的方法,讓做錯事的人認錯,改邪歸正,進而恢復社會和諧。社會運動也在於喚醒民眾提高對於自己或社會議題的認知與瞭解;有些社會運動則在於實際的幫助受害者,幫助人們療傷止痛,恢復人際關係,給人走入世界的能力與意願。
社會運動團體通常需要提出許多計畫與策略以影響更多的人,有致力於國際政治迫害的,如「國際修復式正義」 (Restorative Justice International);有受刑人的,如美國的「正義與和解中心」 (The Centre for Justice & Reconciliation);有社區問題的,如加拿大的「社區正義開跑」 (Community Justice Initiatives),或者挪威國會更通過法律建立「國家和解服務中心」(National Mediation Service);有校園霸淩的,如臺北大學的「橄欖枝中心」。
五、修復式正義是多元策略運用
修復式正義有很多作法,作者認為,透過平等的對話與溝通,以及關係修復或彌補,另外就是恢復人與社會、團體的連結,只要能夠成就這三種功能者,我們都認為是可行的修復式正義做法。
法務部提出了以被害人、加害人的調解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VOM) 的修復式正義,鼓勵對話來達成雙方關係之恢復。只是,法務部調解的作法缺少創造個人與社區團體整合的哲學思想。另外,加害人與被害人不願意見面,也使得法務部推動的方案困難重重,成果相當有限。
加害人、被害人的對話 (victim-offender dialogue),這用於嚴重的犯罪傷害,例如殺人犯罪。這種對話必須由受害人主動提出,犯罪者則仍在監禁,對話的時候,往往還需要一個有經驗的促進者。
面對面會議 (face to face meeting) 也是修復式正義的方法,加害人、被害人,同時也有支持者,例如:家人、朋友,甚至於社區的人,人數不要多多,大家以會議方式進行對話,協商,共同討論衝突發生的事實,帶來的影響,並尋求關係修復可行性的做法。
家庭會議 (family conference) 也是修復式正義的做法。會議由家庭成員依據修復式正義的方法與原則進行,大家面對家庭衝突問題,例如:小孩意見與父母相左,小孩行為偏差,父母生氣,這時,大家在平等與自願的原則之下,分享事件本質,以及帶來的傷害或影響,最後則討論如何面對或解決問題等,家庭會議可以有效解決家庭衝突,成為父母教養之做法。
另外,和平圈 (peacemaking circles) 也是非常普遍的修復式正義作法,除衝突當事人外,也邀請當事人的其他人,例如:間接當事人、支持者、緩衝者,大家圍成圈圈,進行對話,恢復關係,並嘗試提出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和平圈通常需要一個主持人,參與者也必須是自願的;另外,對話過程中彼此都是平等的,沒有階級、身分地位差別的。
- 修復式正義是生命歷程的
Braithwaite提出的修復式正義強調,衝突當事人進行面對面對話、溝通、談判、協商,稱之為修復過程 (the process of restoration),其目的在於使衝突當事人得以療傷止痛,關係修復,進而激勵參與社會的動機,這論點使修復式正義具教育與犯罪預防目的,也成為改變人生的重要生命事件。
另外,修復式正義也在於改變人,尤其是犯罪者,使他們更願意為其行為負起責任,成為不犯罪力量,而這正是修復式正義生命歷程理論典範的價值。
修復式正義的反思與批判
修復式正義有多方面功能,它是確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實踐,也是致力於世界和平的社會運動。另外,修復式正義強調對話與關係恢復的修復過程,這給人走入世界的能力,具有教育上的實用哲學與犯罪學上的預防目的。而就社區或團體而言,修復式正義帶來關係的改善,提升社區、團體的凝聚力與共同情感。
修復式正義必須承認人性的存在,也是修復式正義理論與實作思考的源頭。因為人性,人自私、以自己為中心,人類行為的目的在於帶給自己最大的快樂,如此,社會上才發生競爭、適應、暴力與衝突的問題,這雖然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卻是修復式正義嘗試要解決的課題。
人類還有社會性,人有和人互動的渴望,人也有參與社會的慾望,另外,人追求地位,身分,以及政治、社會角色,這些也是每個人想要的,不管是一般的人或者是犯罪的人,大家都是一樣的;也因此,我們必須重視人類社會性的議題:人不能脫離社會,人類如果不參與社會,就會出現迷亂,變得無所謂,沒有自我控制力,社會對他也沒有控制力。而當缺少了社會連結,一個人就迷失自己,喪失自我規範的力量,各種的表現也就下降,偏差行為出現。如此,作為犯罪學的修復式正義,也必須討論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整合,以及社會連結的問題。
修復式正義理論其實和其他犯罪學理論一樣,乃是學者們對於社會秩序如何維護與建立長期思考得來的結晶。我們知道,古典犯罪學派向舊時代挑戰、力求改革,改革用於契約社會,用懲罰嚇阻犯罪,強調懲罰的快速性及確定性,以建立社會秩序;犯罪學實證學派也在努力找出犯罪原因,以預防犯罪;修復式正義也有相同目的,致力於結合各種犯罪學理論,找出有利於改變人的因素,尤其是建立整合的社區,並透過互動,恢復人際關係,提升犯罪者社會適應能力,參與社會、建立秩序。
Siegel (2011) 對於修復式正義有一些疑慮,包括:(1)其是作為政治的運動,抑或是矯治的過程?然修復式正義應該要定位到較高的層次,超越個人、團體、社會,因為它所追求的是全球的人道價值與和平;(2)應要承認修復式正義有文化與社會的差異。因為修復式正義要如何從多元的社會中找到大家的共識,或者找到共同的修復式正義做法,這是很困難的;(3)平衡犯罪者與受害者的需要,這是相當艱難的事情;(4)修復式正義可能只有短期的效果,忽略了長遠的矯治需要。最後,Siegel也批評,修復式正義的作法未能一致、沒有統一範本,將使修復式正義推動時喪失焦點。
修復式正義在實務執行時,最大的困難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不願意見面,這使推動上困難重重,尤其對於犯罪案件,被害人非常不願意和加害人見面,他們擔心帶來二次傷害。
權力濫用也是修復式正義最頭痛的問題,尤其是學校發生的霸淩事件,家長往往介入,幹預學校處理,處理結果如果不滿意,他們不接受,繼續抗議,或向更高的單位陳情。家長幹預學校的運作十分普遍,作者曾看到小孩在衝突之後,已經沒事,高興的和對方做好朋友,玩在一起,但家長卻放不下,他們堅持要懲罰學生,要老師負責,如果處理不當,他們又持續的向政府部門告訴,使得小小的衝突事件,沒完沒了,學校,無論是校長,老師,同學,家長,都受到不停的困擾,修復式會議在家長幹預下無從召開。
校園安全感以及學生對於團體共同價值的信賴,這些校園環境因素,可以成為修復式正義的實踐的利器,只可惜很多教育工作者忽略其重要性。學校環境如果是有高度凝聚力的,可以提高社會控制力,也有利於修復式會議的推動。相反的,校長不願處理衝突,不想問題擴大,但這結果卻讓大家失去對學校的信賴,往往使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大,不可收拾,老師自然也沒有意願要進行修復式正義的對話了。
媒體的權力,政治的權力,它們都影響修復式正義之公正性,但卻違背修復式正義的工作原則。推動修復式正義實踐時,必須防範,避免權力幹預。
文化上來說,西方人很容易進入圍圈圈 (circle),進行對話,但這在東方社會是較為困難的,衝突的當事人要他們再一起,大家圍成圈圈,來面對面對話,溝通,解決問題,這在東方社會通常是需要一個較高聲望的人,才能夠做得來。不像西方,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有了問題,透過平等的、對話的機制解決。
圍圈圈 (circle) 有時會帶來更大的衝突。之前,我在一個小學進行修復式的會議,我們面對著的問題是一個學生的家長,他要告所有學校的老師,同班同學,以及所有的家長們,當時雙方的衝突可說非常的大。後來在進行修復式會議的圍圈圈對話時,校園裡同樣情景又出現了,學生又在該同學面前,把他們的行為舉止又羞辱了一次,說出他們不喜歡該學生的事情,結果這位同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他爆發了,當場生氣的摔了椅子,極度憤怒的走出教室。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確實有許多挑戰,但寄望本章之說明,有助於幫助讀者找到修復式正義多元,且可行之實踐方案與策略,期能帶來和諧社會,增進人類參與社會的動機。
[1]社會事實是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 (Durkheim) 的概念,強調人類行為受到社會事實的影響,例如:文化、道德規範、社會制度等 (侯崇文,2019)。



